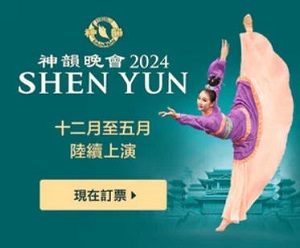有國有家者之座右銘——《貞觀政要》
◎彭忠德
吳兢(670-749年),唐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市)人,品性方直,學通經史,長期擔任史官,以「敘事簡核,號良史」。所著《貞觀政要》影響深遠:後世或書之屏帷、銘之几案,或列之講讀、形之論議。
唐玄宗時,雖然中國社會還沐浴著貞觀盛世的餘輝,但社會危機已不斷產生。
有著見盛觀衰之史家傳統的吳兢,察覺到光明后的黑暗,為使「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再現貞觀之治,便據唐太宗與魏徵等數十位大臣的對話及其奏疏,撰成一部由四十個專題組成的《貞觀政要》進呈給玄宗。雖然書僅八萬字,但卻涉及到當時「人倫之紀」和「軍國之政」等各方面的問題,較為全面地總結了貞觀時代的治國經驗,實為唐初領導者智慧的結晶。
書中在論述統治者和民眾關係時所闡釋的為君、為官之道,正是今人讀《貞觀政要》所要關注的重點。
唐太宗及魏徵等人將正確處理君民關係當作頭等大事。如何為君?第一是重視民眾:首先要認識到國以民為本。魏徵告誡唐太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而唐太宗以史鑒今,也認識到「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猶如饞人自食其身,肉盡必死」。其次要看到民眾的巨大力量。魏徵、岑文本多次向唐太宗進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知民眾之擁戴和反對所導致的結果,唯恐儲君長於深宮而不知其理,與太子乘舟時,便曉以「君舟民水」之論,強調「方為人主,可不畏懼」!
第二是以身作則:首先要看到君主的引導作用。唐太宗請出了古人的「君器民水」之論:「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因此君主要端正自己的一舉一動,「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其次要注意和正人交往,相互勵之以德,才能保證所作之「則」為正道而非邪行。唐太宗認識到,「古人善為國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雖令不從。」
官吏為國與民之樞紐,地位十分重要。如何官稱其職?第一是不貪。為戒絕官吏貪贓枉法,唐太宗十分重視正面引導,多次以珍珠為喻教育官吏:「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對於那些敢於以身試法的貪官,他則毫不留情地施以重刑。正是由於唐太宗「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貞觀年間以命博財的貪官才較為少見。
第二是有能。唐太宗認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貞觀政要》專辟《任賢》一目,著重記載了房玄齡的「明達吏事」、杜如晦的「剖斷如流」、魏徵的「經國之才」等,其用意並非單純地表彰,而是引導文武百官向他們看齊,只有各具其能,各施其能,才能共成治道。
《貞觀政要》還有一個貫穿全書的思想,即諫能安國。各專題的論述大多數是通過進諫和納諫的形式完成的。不論在朝堂上,還是在園苑中,太宗都誠心希望大臣極言切諫,「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為了鼓勵大臣進諫,他往往施以重獎。魏徵曾心悅誠服地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當魏徵因病求退時,唐太宗誠懇地說:「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耶?」將一個時時刻刻挑刺的人留在身邊,限制自己縱情肆欲,唐太宗的這種雅量,不禁使千載之下的讀者油然而生敬意!古往今來,有這種雅量的「第一先生」又能有幾人?進諫不易,納諫更難,唐以後抬棺進諫的事史不絕書,但像唐太宗那樣誠心求諫、虛心納諫,而且從諫如流的人,確實不多。這一差別,恐怕也是導致盛世之治有無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來源:新生網 發稿:200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