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传文化造敦煌(四):藏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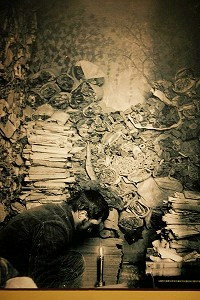
法国人伯希和(网路图片)
◎林洁心
【明心网】六、藏经洞
藏经洞指敦煌莫高窟第17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开凿,是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清朝时,祖籍湖北麻城的王圆荢因生活所迫,流落于酒泉,并在此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后来他云游途经敦煌,登三危山,感慨于莫高圣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便长期居留于此修行。王道士在敦煌四处奔波筹集钱财,用来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并进行修复,仅第16窟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让此秘洞现于世间,他的墓志所云:“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自此,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开始名扬海内外。
(一) 藏经洞中的文献
藏经洞是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其侧面和前侧面画有壶门、衔灵芝的鹿,茶花边饰和云头僧履,坛上泥塑洪辨像。北壁绘两颗菩提树,其左侧画一双手捧持对凤团扇的比丘尼,右侧画一侍女、一手持杖。西壁嵌洪辨告身碑一通。
洞内藏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物5万多件,属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有画有佛像的绢、织物、绣像以及法器等文物不下千件。洞内所藏文献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
1.宗教典籍
在藏经洞的古文献中,佛教典籍约占全部文书的90%左右,可以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合称三藏。这里包括各部典籍和大小宗派的东西,以及同各宗派相关的语言文字的资料,即一卷佛经正面是佛经,背面则是以古印度梵文、窣利文、巴利文等写的佛经原文,用以考证此佛经的来源。洞内有许多失传已久,不为人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经。
据考证,已知敦煌佛经中的佚经有368种之多,其中如《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经典,在印度和中国早已失传。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记载中国佛教史迹、各地佛教情况、吐蕃统治沙州时的佛教源流、敦煌佛寺的规矩等卷。
敦煌文献中道教典籍也颇有数量,主要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纸质优良,书法工整。老子的《道德经》就有大量抄本,多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这一点同70年代出土的银雀山竹简和马王堆帛书《老子》相同。此外,敦煌道教典籍中还有6种《道德经》的注疏,其中《老子想尔注》和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是未被收入的佚本,为后世失传的佳本。
藏经洞还有景教和摩尼教等其它宗教的材料,景教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以后,流行了二百多年时间。景教古经传世极少,鲜有文献记载,而敦煌则保存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典籍以及景教画像一幅,前经还附有景教经典的目录30种。
2.其它文献
敦煌文献包括很多历史地理著作,除部分现存史书的残卷,还有已佚古史书。敦煌在晚唐五代时由归义军统治,这段历史在一些正史中记载简略,藏经洞却有上百种以上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而文献中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朝地理的资料,以及一些史籍未载的西北地区方志,如《沙洲都督府图经》、《寿昌县地境》、《沙洲地志》等。
大量古典文学资料也是敦煌文献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经典和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很多是民间作品。其中所发现之晚唐抄本词曲卷《云谣集》值得一提,《云谣集》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为现存最早唐词抄本集。在藏经洞未开启之前,通常都把赵崇祚在后蜀广政三年(940)编的《花间集》认为是最早的一部词集。
经考证,《云谣集》的发现将这个年代提前到后梁龙德二年(922)。《云谣集》原有两卷,和其它敦煌写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取走,后分藏于英、法国家博物馆。
敦煌唐写本《太公家教》汇集了许多民间谚语,如“居必择邻,慕近良友”,“近妄者陷,近偷者贼。近痴者愚,近圣者名”,“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万顷,不如薄艺随躯”,是唐宋儿童启蒙诵读的格言语录。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印刷术等方面内容,如数学方面的《九九乘法歌》、《算经》和《立成算经》;天文学方面的《二十八星宿位经》、《全天星图》和《紫薇垣星图》;医学类文献有60卷以上,加之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达上百卷,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更保存有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
敦煌文献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其中唐咸通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敦煌文献中还保留了一些琴谱、乐谱、曲谱和舞谱,使后人得以探寻中国古典音乐舞蹈的风采。
此外,文献中有许多与敦煌地区饮食有关的资料,从原料到名称、从制作方法到制作工具,应有尽有,甚至连每种食物的用面数量都记载的清清楚楚。
3.其它文种文献
敦煌文献以汉文居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
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献,是指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但经公元9世纪末代吐蕃灭亡后的百年动乱,经籍文书尽毁,所幸敦煌藏经洞中还存有八至九世纪约数千件藏文写本。但这些藏文资料于1906-1908年分别被斯坦因与伯希和劫往英国和法国。近来,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二) 藏经洞封闭假说
1.避难说
藏经洞在封闭近千年后才得以现世,法国人伯希和根据洞中所藏没有西夏文文书,而其它文书后者为宋初,即公元976-983至995-997年,提出在11世纪前半期,僧人为躲避西夏入侵敦煌,而将所藏经典搬入藏经洞并封闭之。
又有一种说法是11世纪初伊斯兰教的东侵致使藏经洞封闭。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并对于阗佛教以毁灭性的打击。于阗人东逃带来穆斯林东进的消息,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珍贵物品封存洞中(今藏经洞),并做了必要的掩饰。
2.废弃说
英国人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根据他在洞中发现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绢画残片和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等,认为藏经洞是存放这些神圣的废弃物的地方。一些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它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而在藏经洞封闭时,敦煌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典藏理应珍藏于石室中。
3.书库改造说
这种说法由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他在《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文中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中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迄今,藏经洞封闭之谜仍无定论。
中国传统院落式的佛教寺院,一般在南北中轴线上都建有藏经阁,并且大都位于寺院主轴线的结尾。莫高窟原本就是个大寺院,历代修行者不断,不管什么原因有个藏经洞也就不奇怪了。
(三) 世界各地的藏经洞文献
如今,保留在中国的藏经洞文献仅有15000余件,且大多数是佛经,其余皆流失海外。第一个到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献的是英国的斯坦因。
王道士揭开藏经洞的面纱之后,也曾邀请乡绅观看,上告敦煌县,但都没有获得清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加之王道士一心想筹款修复敦煌石窟,正如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他(指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而修复工程巨大,全靠王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
在获得王道士的信任后,自1907年,斯坦因先后三次从王道士手中买下大量的文献,成为获取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这些文献在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后,入藏于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紧接着,精通汉文及数种中亚语言的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以一口流利的汉语获取王道士的好感。时值王道士又需要资金修复洞窟,便同意以藏经洞文献和伯希和作交易。伯希和虽然比斯坦因晚到一年,但由于他拥有丰富的汉学知识,他所获取的文献在数量上不如斯坦因,但却是最精华的部分。现存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
随后,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获取敦煌文献约数百卷,最初收藏在其别墅二乐庄,后因财政原因,逐渐散落在旅顺、首尔、京都等地。
1914年8月,俄国人鄂登堡率团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的文献已所剩无几,鄂登堡收购了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散落在敦煌私人手中的文献,虽然大部分为碎片,但总数有12000多片,现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
(四) 藏经洞的沉思
藏经洞中的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彩,不愧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由文献的语言多样化可见,历史上多个民族的信仰和文化都曾在敦煌交汇。而藏经洞的封闭之时也正是敦煌石窟经历隋唐的辉煌,以及吐蕃、归义军时期的保持,而即将走向衰落的时候,令人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的天意。
在封闭近千年后,藏经洞又奇迹般地被一个道士发现,从而重见天日,而那时中国正处内外交困之中,在各种机缘之下,洞中的文献散落到世界各地,从而使敦煌中保存的中华灿烂文化艺术随即闻名世界,使这个偏远的小地方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一座宝库。这难道又是另一种天意的安排?
文物流失自然令国人痛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正是通过藏经洞文献的流散而为中外学者关注,世界也逐渐认知了东方文化。再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还俗,敦煌的艺术研究者也被要求开荒劳动。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称敦煌研究院)所长常书鸿等人的艺术研究工作陷入停顿。
文革中,常书鸿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包括进行喂猪等劳动。这些风云迭起的政治运动又阻挡了多少研究的进程,毁坏了多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停滞不前的不仅仅是一门敦煌学。
也许有一天,散落在各地的敦煌文献和文物又会在机缘巧合下,汇集在一起,从而将一个真实的敦煌展现给世人。
(本文转载自正见网)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9年8月9日 更新:2009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