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手術刀》作者王立銘:基因編輯是擋不住的
來源:澎湃新聞 記者:王盈穎,文章取自網路,不知是否真假,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2015年,中國科學家首次編輯人類胚胎基因的新聞在全球生物圈炸開了鍋。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搖頭擔憂。
彼時,浙江大學教授、「80后」神經生物學家王立銘以國家「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的身份回國才一年多。他研究動物的神經系統如何控制代謝,作為一種研究工具,基因編輯技術在他的實驗室里經常被應用。為了釐清自己在爭辯中該持什麼態度,他決定寫一寫基因編輯技術的前世今生,最終促成了2017年5月出版的《上帝的手術刀:基因編輯簡史》一書。
5月下旬,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納米樓的一家咖啡店裡,王立銘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就基因編輯這個熱點話題聊了聊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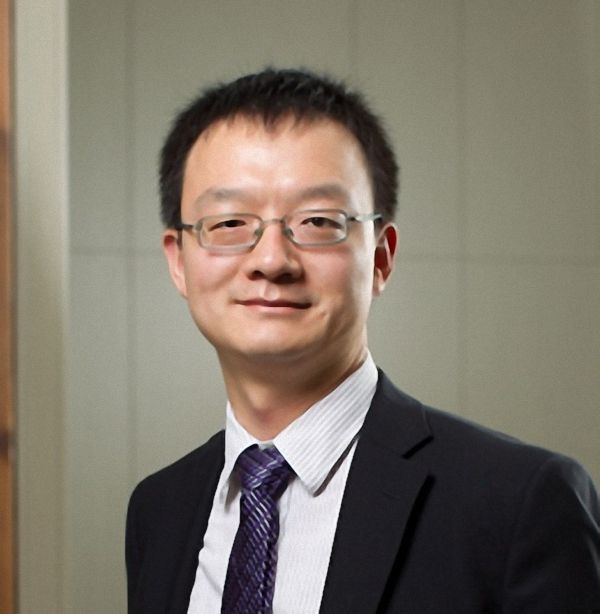
王立銘
聊起基因編輯,正在全球生物實驗室勢如破竹的它總會陷入一個命題:它是帶來福祉的「阿拉丁神燈」還是引起禍端的「潘多拉魔盒」?
對於帶有嚴重遺傳病基因的家庭來說,基因編輯可以修復細胞中的致病基因,是養育健康後代的救命稻草。但也有人惴惴不安,人真的可以僭越自然,對自己的基因進行改造嗎?最後會不會演變為人類用基因編輯製造完美的「超級人類」?
對基因編輯技術一知半解的公眾各執己見。就連科學家,對基因編輯技術也分「比較保守」和「比較開放」兩派,而兩派基於一個共同點:認識到基因編輯是一項革命性技術。
在王立銘看來,基因編輯技術會讓人類社會站在歷史與未來的分界點上。他是開放派,「技術進步只要有益,它總會發生的。我們與其說盡量謹慎,還不如多想點應對的方法。」
王立銘預言,五到十年之內,可能就會有在人類生殖細胞內使用基因編輯技術來治療嚴重單基因遺傳病的臨床應用。所謂單基因遺傳病,指的是受一對等位基因控制的遺傳病。
隨著新一代基因編輯技術CRISPR的出現,基因編輯因為技術門檻低、效率高,在普通生物實驗室就唾手可得。而人類在農耕時代就已經有意識性地培育擁有更好基因的農作物與牲畜,對自身,人類同樣也有追求健康的需求和本能。正是基於這兩點,王立銘認為,基因編輯的發展是「擋不住的」。
但這個判斷並沒有讓王立銘放下對基因編輯技術弊端的擔憂。起初,人們對自身基因進行「動刀」為了治療疾病。但正如王立銘在《上帝的手術刀:基因編輯簡史》中所寫道:「一旦『治療』和『預防』之間的柵欄被打開,『預防』到『改善』的窗戶紙更是一捅就破。」所謂「改善」即「人類增強」,指的是人類用基因編輯來定製身高、容貌甚至智商等非疾病指標,暫時性或永久性地克服人體局限。
從「治療」到「預防」再到「改善」,如同汽車的三個檔位,隨著車速越來越快,誰能說,檔位不會不知不覺地升上去了呢?
「我其實覺得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一件事。」王立銘說:「我們現在這個階段還沒有上檔,應該討論一下上三檔可能會發生的事。」
在和澎湃新聞記者對話時,王立銘說,他看似是開放和謹慎的矛盾體,但「謹慎恰恰是因為開放」。
「不管是恐懼也罷、抵觸也罷、歡迎也罷、漫不經心也罷,我們這個物種在進化數十億年之後,確確實實已經站在了大規模改造其他生物乃至創造自身的門檻上。在這個很可能被載入史冊的關口,與其試圖用道德觀念和倫理批判延緩腳步,還不如用更開放的心態擁抱它,用最嚴格的監管管控它,讓新技術在自身進化成熟之後,幫助人類更好地認識和完善自己。」王立銘在《上帝的手術刀:基因編輯簡史》一書的結尾寫道。
而科學界已經開始未雨綢繆。2月15日,美國國家科學院與美國國家醫學院下屬的人類基因編輯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白皮書,討論基礎研究、體細胞、生殖細胞/胚胎的基因編輯在科學上、倫理上、監管上的問題。
對於頗為敏感的生殖細胞/胚胎基因編輯,他們提出,在嚴格的監管和風險評估下,基因編輯技術應可用於對人類卵子、精子或胚胎的編輯,但僅限於雙方均患有嚴重遺傳疾病的父母,想要健康的孩子卻別無選擇時。編輯生殖細胞/胚胎的基因,這意味著人類的編輯痕迹會世世代代遺傳下去,這是編輯普通體細胞所沒有的意義。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基因編輯技術是發展得太快還是太慢?
王立銘:我覺得應該用水到渠成來形容。在上世紀中葉之前,人類還不知道DNA是遺傳物質,但是從人類文明開始直到那個時候之間的數千年裡,我們的祖先就一直篩選動植物的遺傳性狀,改變它們遺傳性狀。這是人類特別的地方,我們幾千年都一直在做這件事。有了這個強有力的動機,你可想而知,當我們有一天知道什麼是遺傳和遺傳物質的時候,嘗試用更直接和精確的辦法來改變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我們花了幾千年時間來理解基因是怎麼決定遺傳性狀的,但同時我們也有大量工作在研究怎麼改變DNA。只不過當時我們還沒有摸到門道,是在盲目地干這件事。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會馬上下意識地覺得我們應該用更定點、更有目的性的方法(注:即基因編輯技術)來改變它。
從科學史的角度,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甚至可以歷史地說,當我們真的知道DNA是遺傳物質的那一天,距離我們對DNA動刀、改變遺傳信息和生物性狀,就是一瞬間的事。這在歷史上就是一瞬間的事。
澎湃新聞:基因編輯技術可以實現特定基因的插入、敲除、修復,從而進行疾病治療、預防,甚至可能被用來「人類增強」。你對用基因編輯技術來改變人的性狀,是怎麼看的?
王立銘:我的個人傾向是:第一,我還是比較開放的。人類這一願望是合理的,技術門檻也沒有那麼高,從動機到手段都很難被壓制。歷史地看,從來都是科學技術在改變倫理觀念,而不是倫理觀念在改變科學技術。
第二,有地方需要謹慎。謹慎不是說面對新技術的出現本能的小心,而是說一些具體原因。
首先是技術上,除了脫靶效應(注:所謂脫靶,指的是基因編輯工具工作時,可能「傷及無辜」,除了人們想改變的目標基因外,無意中改變了其他基因)等,比較現實的是,不管是改變容貌還是改變智商,我們還不知道具體有哪些基因參与了這些。
以智商為例,我們現在很多研究證明,智商很大程度上是遺傳決定的,這是早就知道的,但我們並不知道是哪些基因來決定。可能有幾十、上百個基因,這些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想象是非常複雜的。最終即便有一個人說想要通過基因組信息來設計智商,他也無從下手——不知道改哪些基因,也不知道改了之後會產生什麼副作用。因為那些基因不光是影響智商,也影響很多其他東西。
人類的複雜性狀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搞清楚,我覺得不太好說。這是技術上最大的一個障礙。
除了技術上的謹慎,我的觀點是,基因編輯技術不管用於治療、預防還是改善,都有一個問題是可能會影響人類基因庫的多樣性。
舉個例子:最早會上臨床的疾病可能有鐮刀型貧血或者地中海貧血,它們是一個血紅蛋白基因出了問題才會得病。它們的遺傳因素比較簡單,患者比較痛苦。美國科學院的白皮書里提到了這兩種病。但即便是它們,我們也會意識到一個問題:鐮刀型貧血的基因缺陷為什麼會出現?(其實)是因為它能抗瘧疾。在人們發現青蒿素之前,人的祖先就靠這個來抗瘧疾。
人類現在已經有了那麼多抗瘧疾的藥物,可能認為這個基因變異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放到那個時候,這個基因變異是救命的。反過來講,今天我們覺得一個基因是有害的,會不會在很多年之後,對於人類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把它都改造的,以後會不會有問題?
以此類推,如果我們真的按照我們這一代人接觸到的主流價值觀來修改孩子的遺傳信息,那麼我們這一代人的價值觀就固化在基因庫里。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
第三個需要謹慎的是不平等。人類社會從來也沒有平等過,財富的不平等甚至還能通過教育傳到下一代,但至少這都是有可塑性的,不管是屌絲逆襲還是富不過三代,這都存在。但(修改生殖細胞/胚胎的)基因組這事沒有可塑性,修改成什麼樣,不出意外它就一直遺傳下去。社會地位高的人會把他們的後代修改得一代比一代更有競爭優勢。那窮人就沒法翻身了,導致階層永久性固定。這是比較可怕的事。
澎湃新聞:除了加強政府監管,還有什麼可以未雨綢繆,應對這些需要謹慎的地方?
王立銘:我其實不覺得有什麼更好的辦法。這相當於我們要想辦法來約束人的本能。
我在討論政府監管的時候,隱含的意思是不全禁止,完全禁止就不是監管了。我認為完全禁止是不對的,因為會滋生黑市的交易,會使得技術風險很難控制,會變得很危險。另一個也更加使得只有社會地位比較高、能接觸到一般人接觸不到的禁區的人才能享用,老百姓不能接觸。
所以與其這樣,還不如有限度地開放。「監管」在我的語境里,是有限度的開放,換取大家老老實實在一個區域里,到指定的醫院做,(規定)什麼樣的疾病可以做(基因治療),什麼樣的疾病還要等一等。說到監管我是希望實現這樣的效果。
對基因治療的監管體系不需要新的,只要嚴格按照我們對藥物、醫療器械監管的程序就可以了。做臨床研究后提出臨床申請,審批通過就可以進行臨床試驗。
澎湃新聞:2015年,中山大學教授黃軍就發表第一篇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的報告,引起了學界很大的轟動。目前,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腫瘤科主任盧鈾正在進行對肺癌病人的CRISPR臨床治療,也是世界首例。有一些國外的科技媒體在報道中國關於基因編輯的突破性舉動時,有時會提到相比于歐美國家,中國的醫學倫理要求比較低,所以會允許做這些歐美國家無法做的大胆試驗,進行一些全球首例。你認同嗎?
王立銘:這是沒有道理的。第一,有史以來,「第一例」的事可能是中國沒有歐美來得多。圍繞著生物的倫理爭議,包括重組DNA、克隆、胚胎幹細胞研究,這些都和中國沒有什麼關係,那時候中國的生物學還很落後。突破倫理做研究,這是人類的本能。從來都是科學技術在改變倫理觀念,而不是倫理在限制科學技術。這句話隱藏的意思是,科學發現在一次一次突破倫理。
第二,關於倫理這事,本來就是文化性的。在中國,如果一個孕婦做超聲檢查,發現嬰兒有些殘疾,醫生會建議流產,孕婦也會接受。但是在天主教國家,這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懷孕生子是上帝的旨意,對胎兒進行任何操作被認為是反倫理的。這在中國不覺得是違反倫理的,不然中國的電視上做流產廣告就不會覺得很正常了。
談到倫理問題時,不同文化的看法可能一樣,可能不一樣。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對一種事物,你的倫理觀覺得OK,我的倫理觀覺得不OK,這不說明我們比你奇怪或落後。
當然了,我們對於很多事情也可以有共同的底線,比如不能隨便剝奪生命,等等。這裏面可能也包括,我們此時都覺得對生殖細胞/胚胎的基因進行改變需要特別謹慎。
第三,具體操作層面,在中國做一些實驗是不是比西方更松?我猜想可能會有。畢竟中國引入倫理監管機制建立得確實比較晚。在很多細節上管理的可能確實會更松(一個例子就是魏則西事件。他所接受的細胞療法在美國早已是廢棄不用的辦法。)但是我的看法是,我們最好就事論事討論這個監管問題。如果能拿出證據來說我們在一些地方比較松,可以接受,可以改。但要是僅僅因為中國的醫院和科學家在做一些新東西出來,這些新東西可能因為種種原因歐美沒有很快開始做,因此說是因為我們的倫理比較松,這是我不同意的。

